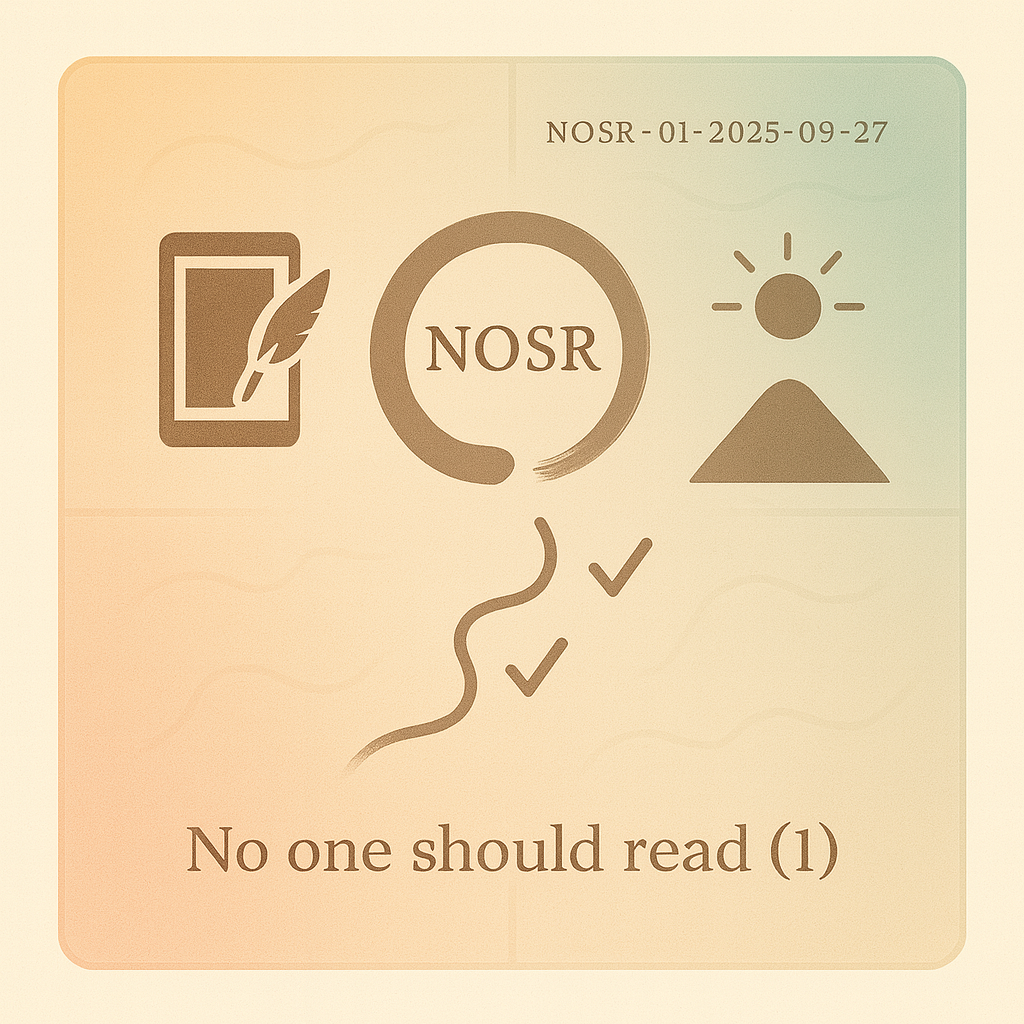
无人问答
懦弱
读了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和《生活在低处》。当然作者描述的生活细节离开我是很远的。但他简单粗暴的文笔和纪实文学,让我有种刮骨疗伤的感受。我于是去看了他的访谈,作者说自己是一个本质懦弱的人。当然,一个向大家讲述自己生活和内心的人,与懦弱似乎矛盾。我想他应该是很细腻,享受自我,又对外界毫无期待的人。我想他应该也是自由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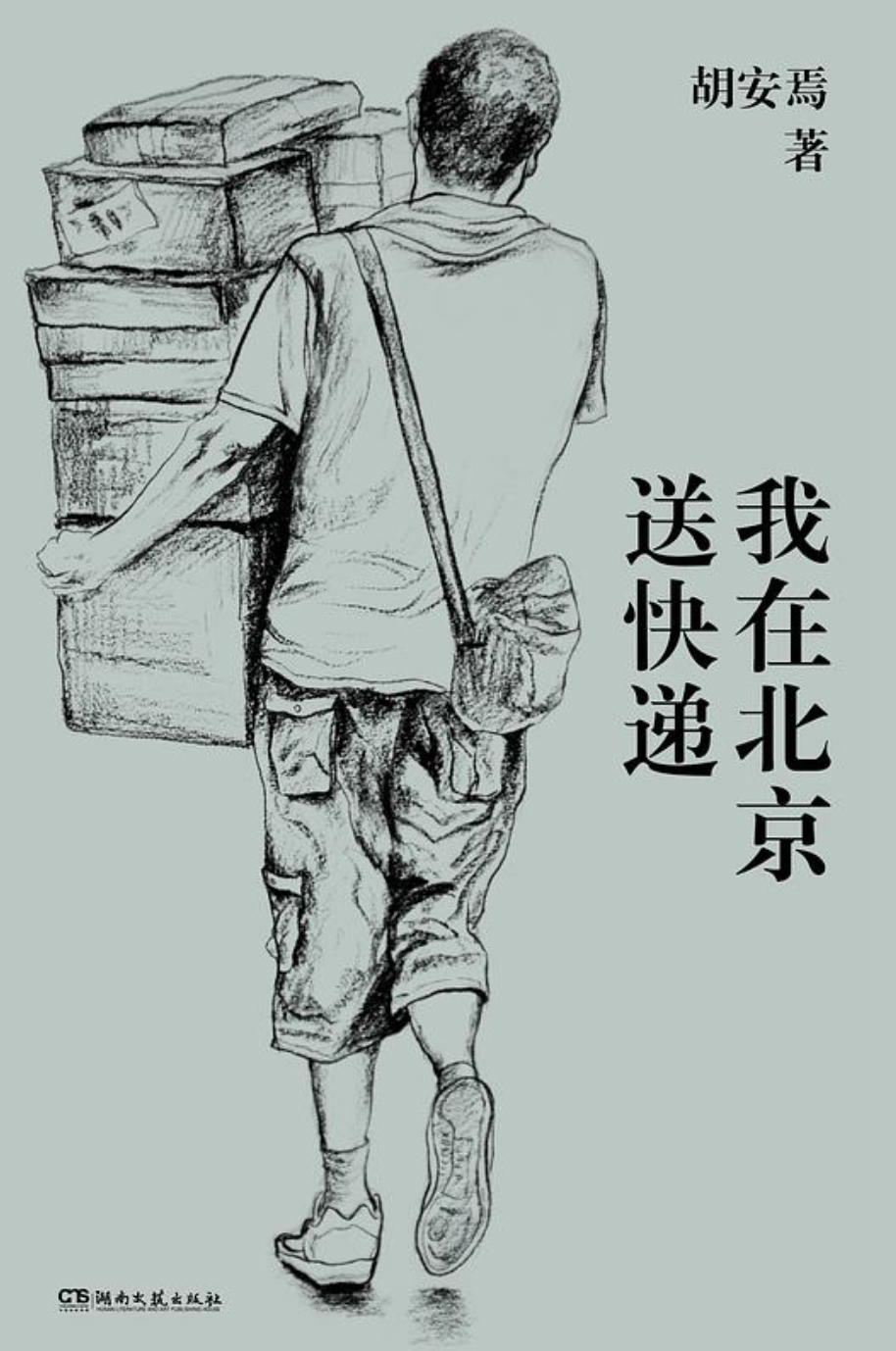
就像,写下 “离开” 和 “走开” 两个动词,后者显得毫无期待。“我离开了”显得有人期待你原本在那,也有人期待你的到来。这种懦弱是将自己与外界分离。胡安焉在对外界不抱任何期待的同时,将日常记录下来。对着黑暗的呐喊,就只有呐喊,没有回声。
这种懦弱的反面不像是勇敢,更像是某种“主人翁”精神,似乎应该把世界当成一个游乐园,所有人的存在都可以被随意赋予意义。

口袋
我在等红绿灯,车停在第一排,能看到路口的一对男女。他们很平常地拥吻。女生穿着牛仔裤,手机插在左后边的裤兜里。绿灯了,汽车道会比人行道晚几秒钟。男生牵起女生的左手,举在胸口位置。走到马路中间,女生用右手背过去,使劲想要确认手机还在。也就几秒钟,然后他们就走开了。除了无聊在等绿灯的我,是没有人会在意的。当然,情感似乎也应该是不被在意地,是不经意地,是生理性地。
小时候的夏天里,收到一盒好吃的巧克力,每一颗拇指大小。但我总能用牙齿一点点咬下,每一小块都会慢慢用舌头抿碎,慢慢融化。这样,一块巧克力的快乐就会被无限延长。一般吃掉一两颗,我会再拿一颗放在口袋里,就出去和朋友玩了。家里是没人跟我抢巧克力,但放在口袋里便让我触手可及。天很热,我其实通常会忘了它在口袋里。回到家就发现,巧克力早在口袋里融化,黏糊糊的。我就随手把裤子丢在洗衣篮里,也并不会感到惋惜,因为口袋里的巧克力,被我留在了那些下午里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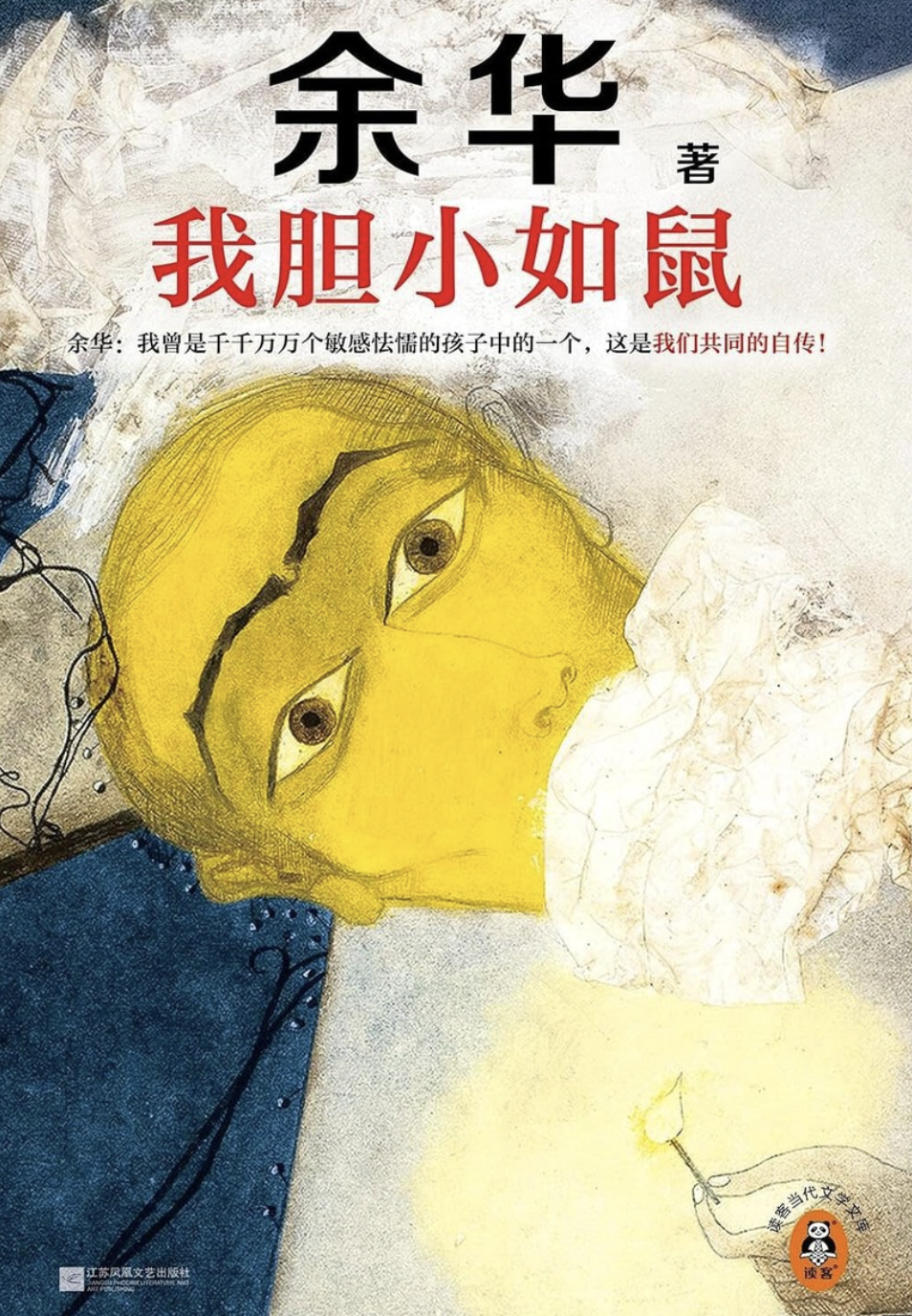
羊羔的父亲
半夜刷手机的时候,会有七七八八的推送。人工智能按照作息预测,把一些消除负面情绪的消息写在了最前面。我猜,模型毫不留情地把我预测成了文艺青年,满屏余华尔尔的推送。关于讨论懦弱,《我胆小如鼠》里有这样一段描写羊羔的父亲,大致如下。羊羔的父亲是一个胆小的卡车司机。他有一个习惯,半夜开车的时候,会摇下车窗,向外大喊"你找死啊"。有一次,羊羔和父亲坐在卡车里,遇到一辆拖拉机,车上的人皮肤黝黑。羊羔的父亲壮胆,向窗外喊"你找死啊"。然后猛踩油门。他的父亲知道,拖拉机是追不上卡车的。
这段描写似乎阐述了关于勇敢的一层含义。当你的行为,面对的是你已知的结果时,你向他人展现出的并不是勇敢。当然,这也不像是懦弱。这就像平常夏天喝掉冰镇的可乐,气泡对于口腔的刺激,转瞬即逝。

抓猫
从小住校,学校配置很好,培养出两个恶习:早饭期待很高,也从会想着夜宵。食堂有三层,还有一个饭店可以点菜,大概是给校领导用的。有个暑假,跟同学拿着零花钱,就会天天去点跑蛋。早餐是早起的动力之一,葱油拌面加蛋。甚至我觉得所有人都会记得葱油拌面师傅的做法。面下在篓里,然后碗里有葱油,最后加入煎蛋。因为住校,同学是永远一起走的。有一次,大概是初一的时候。我们在热水壶楼和澡堂楼后面,篮球场前面,遇到了一只野猫。几个人决定拿塑料袋抓猫。围成一圈,将猫逼入墙角,然后装进塑料袋里。抓完后,我们才开始讨论应该放在谁的寝室。大概养了两三天。那几天,满走廊都是猫的味道,我们以为能骗过宿管,自欺欺人。那几天,我们会趴在地上,看躲在下铺床底下的猫。没过几天,猫就跑了,不知道是宿管放跑了,还是自己走了。猫有九条命,我想从窗户下跳下去,大概也死不了。